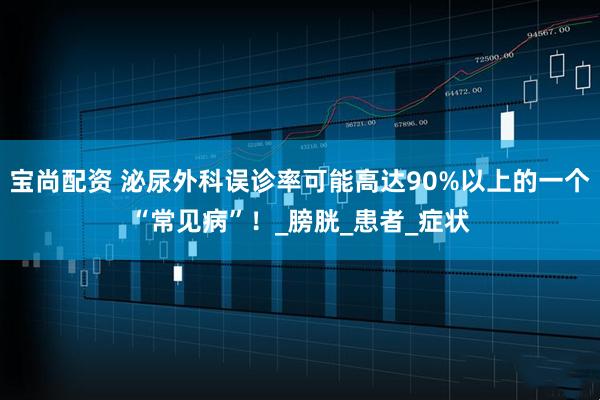
宋宝林谈泌尿
专注泌尿系健康 值得您长期关注
公众号
个人微信
我的网站
抖音
间质性膀胱炎是什么?
定义、病因与发病机制
在宁静的深夜,一些人却因膀胱的刺痛频繁起身,奔波于卫生间。这种反复折磨的痛楚背后,潜藏着一种常被忽视的疾病——间质性膀胱炎(Interstitial Cystitis),也称膀胱疼痛综合征(BPS)。它并不罕见,却如“隐形的疼痛”一般在大众视野之外广泛存在。据统计,美国有调查显示6%–11%的女性和约2%–5%的男性报告过类似IC/BPS的症状。然而令人震惊的是,这些符合IC/BPS症状标准的人群中,只有不到10%曾被确诊为IC/BPS。在我国,专家估计IC/BPS的误诊率可能高达90%以上——也就是说,绝大多数患者长期承受着痛苦却未能得到正确的诊断与治疗。由此可见,间质性膀胱炎是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普遍,却更容易被漏诊或误诊的疾病。
展开剩余96%那么,究竟什么是间质性膀胱炎?医学上将IC/BPS定义为一种以膀胱相关的慢性疼痛为特征、伴有下尿路症状且找不到其他明确原因的综合征。简而言之,患者会长时间(通常至少6周以上)感到膀胱或盆腔区域的不适(疼痛、压迫或灼痛感),伴随尿频、尿急等症状,但小便检查和培养并没有感染或其他明显异常。这一点很关键:IC/BPS是一种诊断排除性疾病,必须首先确定不存在尿路感染、结石、肿瘤等其它原因,才能考虑IC/BPS。正因如此,IC/BPS常被称为“特殊的慢性膀胱炎”,其特殊之处就在于病因不明且检查往往“正常”,但患者的痛苦却是真实而深刻的。
在医学研究中,IC/BPS的确切病因迄今尚未明了。就像一团解不开的谜,科学家提出了多种理论却都不足以完全解释这种疾病的全部面貌。目前较为广泛接受的学说包括:膀胱黏膜保护层(糖胺聚糖层)缺陷导致尿液中刺激性物质渗入膀胱壁引发炎症、上皮通透性增高使膀胱壁“漏洞百出”、肥大细胞异常活化和神经源性炎症引起一系列慢性疼痛反应,以及自身免疫反应等。换句话说,IC/BPS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:膀胱内壁屏障受损,让本不该接触膀胱肌层的刺激物“伤了膀胱的心”;免疫细胞和神经系统卷入其中,在膀胱组织内发动“战争”;久而久之,膀胱壁出现慢性炎症和纤维化,容量减少,传递出疼痛信号。然而,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单独解释所有患者的症状,因此IC/BPS仍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、异质性的疾病。正因如此,它也成为泌尿外科领域的一大难题。尽管病因成谜,但可以确定的是:这种疾病对患者生活的影响绝不亚于癌症。有调查表明,IC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甚至低于慢性肾衰竭患者。这无疑提醒我们:不要让“隐形的疼痛”被忽视,它需要被科学认识和重视。
主要临床表现
膀胱在疼痛中呼喊
如果说正常人的膀胱如温顺的容器,那么IC/BPS患者的膀胱则仿佛变成了一只“易怒的猛兽”,轻易就会以疼痛和不适来抗议。膀胱疼痛是IC/BPS最核心也几乎每个患者都会经历的症状。这种疼痛多位于下腹部、膀胱区或会阴盆腔区域,女性常感觉疼痛出现在耻骨上方或阴道与肛门之间的深处,男性则常在阴囊和肛门之间感到针刺样的痛楚。疼痛程度因人而异,可以是隐隐的不适,也可以剧烈如刀割般难忍。一个典型特点是:当膀胱逐渐充满尿液时,患者会感到疼痛或强烈的压迫不适感,而排空小便后这些不适往往暂时缓解。这种“膀胱充盈痛,排尿后缓解”的现象被很多患者形容为“膀胱在呼喊”:憋尿时疼痛加剧,仿佛膀胱在抗议需要释放;一旦如释重负地排尿,疼痛便随之减轻。然而,好景不长,随着新的尿液产生,疼痛又卷土重来,周而复始,令人身心俱疲。
除了疼痛,尿频和尿急也是IC/BPS的主要临床表现。患者几乎无时无刻不被尿意困扰,总感觉“尿憋不住”、“尿没排干净”。他们白天黑夜跑厕所的频率远超常人:常常白天和夜间总计加起来如厕数十次,重症者甚至一天高达50~60次!而每次排尿量却很少,往往刚排没多久又急切地想上厕所。这种持续的尿急使患者难以从事正常的工作和社交活动:刚坐下不久又得站起,睡梦中频频被尿意唤醒。一位患者打趣道:“我的生活被定在了厕所和床之间来回摆荡。”正是这种夸张的尿频尿急,使IC/BPS在外人看来有点像普通的膀胱炎或“跑厕所综合征”。但与单纯的功能性膀胱过度活动(OAB)不同的是,IC/BPS的尿频尿急往往伴随疼痛,患者是为了减轻疼痛而频繁排尿;而OAB患者则多因避免尿失禁而紧急如厕。这一细微差别成为鉴别两者的重要线索。此外,由于长期睡眠被打断,患者白天疲惫不堪,情绪也受到影响,焦虑和抑郁常相伴而生。
某些IC/BPS患者还可能出现性交疼痛(特别是女性)。亲密生活因此受到严重干扰,患者及伴侣都承受心理压力。女性患者的症状有时在月经期前后加重,男性则可能在射精后感到疼痛骤增。很多患者报告,症状有周期性波动,时好时坏:有时缓解一阵,让人以为痊愈在望;不料下一刻又卷土重来,甚至某些诱因会让症状雪上加霜——比如吃了辛辣刺激的食物、饮用了咖啡酒精等饮品后,疼痛和尿意常常骤然加剧。久坐不动、长途旅行憋尿、过度劳累、心理压力大时,症状也容易复发或恶化。这些触发因素犹如点燃膀胱的导火索,让患者平日小心翼翼地调整生活方式,唯恐招惹“膀胱里的火山”喷发。
需要强调的是,IC/BPS的症状虽与慢性尿路感染极为相似——都是尿频、尿急、下腹疼痛,但IC/BPS的尿液化验和培养往往是阴性,不存在感染病原体。正因如此,不明就里的患者和医生有时会反复当作“尿路感染”来治疗。当抗生素一轮轮下去却不见效时,焦虑与绝望便在患者心中滋长。这种“疼痛无人懂、检查又正常”的处境,使许多IC患者饱受误解,在确诊之路上四处奔波。这隐秘而剧烈的症状组合,是IC/BPS发出的呼救信号,也是我们深入了解这一疾病的起点。
容易混淆
IC/BPS与其他疾病的误诊及鉴别
间质性膀胱炎常被称为“医学谜题”,不仅因为它本身复杂多变,还因为它极易与其他疾病混淆。患者初次就诊时的症状并没有特异性,很容易让医生联想到更常见的病。例如,一个女性患者反复下腹痛、尿急尿频,医生首先会考虑尿路感染或妇科炎症;男性患者骨盆疼痛、排尿不适,则常被诊断为前列腺炎。在临床实践中,这种复杂性导致了严重的误诊、诊断不足和延迟诊断。我们来看看IC/BPS最容易“撞脸”的几个疾病,以及如何将它们区分开来:
慢性尿路感染:这是IC/BPS最容易被误认为的疾病之一。二者症状几乎难分伯仲——都是尿频、尿急、尿痛甚至血尿。但是区别在于:真正的细菌性膀胱炎/尿路感染在尿常规和尿培养中能查出致病菌阳性,而IC/BPS患者的尿液检查通常无菌。换言之,IC/BPS是一种“无菌性炎症”。在一项研究中,高达74%的IC早期患者最初被误诊为尿路感染,反复使用抗生素却收效甚微。如果遇到“典型尿感症状但化验总是阴性”的情况,就要警惕IC/BPS的可能了。
慢性前列腺炎/慢性盆腔痛综合征(CP/CPPS):这是男性IC/BPS患者的常见误诊。很多男性患者在确诊IC之前,往往多年被当作前列腺炎治疗。两者症状确实非常相似:男性III型前列腺炎(尤其III B型非细菌性前列腺炎)典型表现为会阴、耻骨上区、睾丸或阴茎等处的疼痛不适,排尿或射精后疼痛往往加重,同时伴有尿频、排尿不尽感等下尿路症状。这些临床特征与IC/BPS十分类似,以至于部分男性可能同时符合两种疾病的诊断标准。鉴别要点在于疼痛的来源和伴随特征:前列腺炎引起的疼痛多被定位在前列腺及其邻近区域,直肠指检时前列腺可能有压痛,部分患者前列腺液检查可见炎症细胞;而IC/BPS的疼痛更偏向膀胱充盈引发,男性如果出现“疼痛性尿急”或“膀胱充盈痛”这类明显与膀胱有关的症状,应强烈考虑IC/BPS。此外,前列腺炎患者常有射精痛和性功能障碍,而IC/BPS患者的性疼痛更多发生在女性或与膀胱充盈状态相关。需要指出的是,有时确实存在前列腺炎与IC/BPS并存的情况,对于这些重叠患者,治疗需要双管齐下。临床上,一项针对男性IC的研究发现,有17%的病例同时符合IC和CPPS,两者在男性中的患病率和症状谱高度重叠。这提示医生在面对疑似前列腺炎而疗效欠佳的男性时,也要打开思路,考虑IC/BPS的可能。
膀胱过度活动症(OAB):IC/BPS与OAB的共同点是都有尿频尿急,但两者有本质区别。OAB是一种以急迫性尿失禁倾向为特点的综合征,患者强烈的尿意主要是怕憋不住尿导致漏尿,而IC/BPS患者的尿急则源于疼痛或不适感。简言之,IC是“痛得非尿不可”,OAB是“急得非尿不可”。另外,IC患者排尿后有疼痛缓解感,而OAB患者排尿后更多的是如释重负但并无疼痛变化。两者的膀胱镜检查也不同:IC/BPS可能看到膀胱黏膜损伤、出血点甚至溃疡,而单纯OAB的膀胱通常外观正常。尿动力学上,OAB患者常表现出逼尿肌不自主收缩,而IC/BPS患者则可能膀胱容量小且在低容积时就出现强烈尿意甚至疼痛。区分这两种疾病对治疗方案影响很大:OAB偏重使用抗胆碱能药物等放松膀胱平滑肌的治疗,而IC/BPS则需要抗炎镇痛、修复膀胱黏膜为主的治疗。
慢性盆腔炎(女性)和其他妇科疾病:部分女性IC患者的症状(慢性盆腔痛、性交痛、尿频等)容易被归咎于妇科问题。例如慢性盆腔炎(通常由反复的妇科感染引起)会导致下腹及盆腔疼痛,并可能伴有月经异常、白带增多等表现,而IC/BPS通常不伴有明显的妇科症状。鉴别要点在于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指标:慢性盆腔炎患者常在妇科盆腔检查时发现子宫附件压痛、增厚粘连等,超声可能提示输卵管粘连或积水,炎症指标如血沉、C反应蛋白有时升高;而IC/BPS的妇科检查往往无异常发现,痛点更多在膀胱区域,尿液检查无感染。此外,一些特殊情况也要与IC/BPS鉴别,例如膀胱肿瘤(尤其是原位癌)和尿路结石也可能引起膀胱刺激征和疼痛,因此对血尿明显或危险因素(如吸烟史)的患者,必须进行尿液细胞学和影像学检查以排除肿瘤。正因为IC/BPS是排除性诊断,医生需要耐心而严谨地将这些可能的“李鬼”一一排查,在排除了细菌感染、结石、肿瘤、异物以及其他盆腔病变后,IC/BPS的诊断才水落石出。
慢性尿路感染:这是IC/BPS最容易被误认为的疾病之一。二者症状几乎难分伯仲——都是尿频、尿急、尿痛甚至血尿。但是区别在于:真正的细菌性膀胱炎/尿路感染在尿常规和尿培养中能查出致病菌阳性,而IC/BPS患者的尿液检查通常无菌。换言之,IC/BPS是一种“无菌性炎症”。在一项研究中,高达74%的IC早期患者最初被误诊为尿路感染,反复使用抗生素却收效甚微。如果遇到“典型尿感症状但化验总是阴性”的情况,就要警惕IC/BPS的可能了。
慢性前列腺炎/慢性盆腔痛综合征(CP/CPPS):这是男性IC/BPS患者的常见误诊。很多男性患者在确诊IC之前,往往多年被当作前列腺炎治疗。两者症状确实非常相似:男性III型前列腺炎(尤其III B型非细菌性前列腺炎)典型表现为会阴、耻骨上区、睾丸或阴茎等处的疼痛不适,排尿或射精后疼痛往往加重,同时伴有尿频、排尿不尽感等下尿路症状。这些临床特征与IC/BPS十分类似,以至于部分男性可能同时符合两种疾病的诊断标准。鉴别要点在于疼痛的来源和伴随特征:前列腺炎引起的疼痛多被定位在前列腺及其邻近区域,直肠指检时前列腺可能有压痛,部分患者前列腺液检查可见炎症细胞;而IC/BPS的疼痛更偏向膀胱充盈引发,男性如果出现“疼痛性尿急”或“膀胱充盈痛”这类明显与膀胱有关的症状,应强烈考虑IC/BPS。此外,前列腺炎患者常有射精痛和性功能障碍,而IC/BPS患者的性疼痛更多发生在女性或与膀胱充盈状态相关。需要指出的是,有时确实存在前列腺炎与IC/BPS并存的情况,对于这些重叠患者,治疗需要双管齐下。临床上,一项针对男性IC的研究发现,有17%的病例同时符合IC和CPPS,两者在男性中的患病率和症状谱高度重叠。这提示医生在面对疑似前列腺炎而疗效欠佳的男性时,也要打开思路,考虑IC/BPS的可能。
膀胱过度活动症(OAB):IC/BPS与OAB的共同点是都有尿频尿急,但两者有本质区别。OAB是一种以急迫性尿失禁倾向为特点的综合征,患者强烈的尿意主要是怕憋不住尿导致漏尿,而IC/BPS患者的尿急则源于疼痛或不适感。简言之,IC是“痛得非尿不可”,OAB是“急得非尿不可”。另外,IC患者排尿后有疼痛缓解感,而OAB患者排尿后更多的是如释重负但并无疼痛变化。两者的膀胱镜检查也不同:IC/BPS可能看到膀胱黏膜损伤、出血点甚至溃疡,而单纯OAB的膀胱通常外观正常。尿动力学上,OAB患者常表现出逼尿肌不自主收缩,而IC/BPS患者则可能膀胱容量小且在低容积时就出现强烈尿意甚至疼痛。区分这两种疾病对治疗方案影响很大:OAB偏重使用抗胆碱能药物等放松膀胱平滑肌的治疗,而IC/BPS则需要抗炎镇痛、修复膀胱黏膜为主的治疗。
慢性盆腔炎(女性)和其他妇科疾病:部分女性IC患者的症状(慢性盆腔痛、性交痛、尿频等)容易被归咎于妇科问题。例如慢性盆腔炎(通常由反复的妇科感染引起)会导致下腹及盆腔疼痛,并可能伴有月经异常、白带增多等表现,而IC/BPS通常不伴有明显的妇科症状。鉴别要点在于妇科检查和实验室指标:慢性盆腔炎患者常在妇科盆腔检查时发现子宫附件压痛、增厚粘连等,超声可能提示输卵管粘连或积水,炎症指标如血沉、C反应蛋白有时升高;而IC/BPS的妇科检查往往无异常发现,痛点更多在膀胱区域,尿液检查无感染。此外,一些特殊情况也要与IC/BPS鉴别,例如膀胱肿瘤(尤其是原位癌)和尿路结石也可能引起膀胱刺激征和疼痛,因此对血尿明显或危险因素(如吸烟史)的患者,必须进行尿液细胞学和影像学检查以排除肿瘤。正因为IC/BPS是排除性诊断,医生需要耐心而严谨地将这些可能的“李鬼”一一排查,在排除了细菌感染、结石、肿瘤、异物以及其他盆腔病变后,IC/BPS的诊断才水落石出。
总之,IC/BPS常常蒙着别的疾病的面纱,让人误入歧途。据报道,IC患者从出现症状到最后确诊,平均可能历经数年之久,期间辗转多科、多次误诊。有的患者被当作精神心理问题处理,有的则被简单归为更年期不适、膀胱神经官能症等。提高对此病的认识,正是为了尽早揭开误诊的面纱。幸运的是,如今越来越多的指南和专家共识开始强调IC/BPS的鉴别诊断,提醒临床医生“凡顽固性膀胱刺激征+盆腔疼痛而找不到明确原因者,当心IC/BPS”。只有主动将其纳入鉴别诊断列表,才能减少漏诊误诊,避免患者经历不必要的治疗延误之苦。
诊断标准
权威指南中的IC/BPS
如何确诊间质性膀胱炎?既然没有特异性的化验指标,又症状多与他病重叠,临床上主要依靠一套全面细致的评估和排查流程。针对这一点,国内外权威学会制定了诊断指南,为医生提供了宝贵的“侦破”思路。
美国泌尿外科学会(AUA)指南是IC/BPS诊治的重要参考之一。AUA于2011年首次发布IC/BPS指南,之后在2014年和2022年进行了修订更新。根据AUA指南:对疑似IC/BPS患者的基本评估应当包括详尽的病史采集、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必要的实验室检查。病史中医生会询问症状持续时间(IC一般要求症状至少持续6周以上,体现其慢性特征),以及症状的详细特点——每天排尿的次数,是否存在夜尿;尿急的强烈程度和性质,是否因为疼痛而急迫(即“疼痛性尿急”);盆腔疼痛/不适的部位、性质和强度,是否因膀胱充盈而加重、排尿后缓解**。这些特征性的描述(比如“憋尿痛”“尿后舒适期”)对于诊断IC至关重要。此外,医生还会了解患者有没有上述提及的诱发因素、既往有无相关疾病史。体格检查方面,重点检查腹部和盆腔:腹部按压是否有膀胱区域的压痛或包块;盆腔检查需评估女性阴道、男性前列腺的情况,以及男女患者的尿道口是否异常、盆底肌肉有无压痛痉挛等。这些检查是为了排除阴道炎、尿道炎、前列腺疾病或盆底肌肉疼痛综合征等其他原因。实验室检查则少不了尿常规和尿培养,即便尿常规阴性,有经验的医生也常会送尿液培养,以确保没有漏掉低程度的隐匿感染。同时,对于出现血尿的患者应按血尿的常规诊疗途径进一步做影像学检查,以排除结石或肿瘤。可以看出,AUA指南强调先证实IC/BPS典型症状,再排除其他疾病这一“双重要求”,这也是IC/BPS诊断的金标准思路。
当初步评估指向IC/BPS且没有证据支持其他疾病时,即可基本确立诊断。而膀胱镜检查往往被视为诊断IC/BPS的重要辅助手段。AUA指南指出:对于典型、无并发症的IC/BPS患者,膀胱镜或尿动力学并非确诊的必需条件(也就是说,不需要“镜下见病”才能诊断)。然而,在诊断存疑或症状非典型时,应考虑进行膀胱镜检查和/或尿动力学检查以帮助鉴别。特别地,如果临床怀疑存在Hunner病变(Hunner溃疡),那么膀胱镜检查是必须的**。膀胱镜检查通过一根带摄像头的细管伸入膀胱,可以直接观察膀胱内壁情况,是发现IC/BPS特异性病变的“火眼金睛”。经典的IC膀胱镜下表现包括:膀胱黏膜弥漫性充血、水肿,轻度充盈时即出现广泛的点状出血(肾小球出血或称Glomerulations);在一些重度患者可见Hunner溃疡(亨纳病变),表现为膀胱壁的局部充血裂隙或片状溃疡,常位于膀胱穹窿或壁部。同时,由于慢性炎症导致纤维组织增生,膀胱弹性变差、容量明显缩小,这在镜检时可通过测量麻醉下膀胱最大容量来证实。这些膀胱镜下发现对IC/BPS的诊断有重要支持作用:发现Hunner溃疡几乎可以确认诊断,而仅有弥漫性出血点则需结合症状综合判断。需要注意的是,一些早期或非典型IC患者膀胱镜检查结果可能正常,这并不能排除IC。因此,膀胱镜更多是用于排除其他病变、发现特异病变,而不是IC的必备诊断标准。同理,尿动力学检查有助于了解膀胱功能(如容量、顺应性、逼尿肌活动),以排除膀胱颈梗阻或逼尿肌过度活动症等问题;但尿动力检查在IC/BPS中往往缺乏特异性,其发现(如低容量时即出现强烈的尿意,伴或不伴不自主逼尿肌收缩)并非IC所独有。因此尿动力仅在复杂病例中起辅助作用。综上,IC/BPS的诊断依赖于临床症状为主、排除为辅、膀胱镜等检查佐证的原则。这一路径虽复杂,却是为了不错诊每一位患者:正如AUA指南所言,如果多次治疗无效,应重新考虑IC/BPS诊断——提醒临床医师持续验证诊断,避免误诊他疾或漏诊IC的风险。
在欧洲泌尿外科学会(EAU)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指南中,对IC/BPS的定义和诊断流程与AUA总体一致。EAU将其归类为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的一种,使用“膀胱疼痛综合征(BPS)”这一术语,定义也强调持续的盆腔/膀胱疼痛伴尿路症状且无感染证据。早期国际尿控学会(ICS)的标准要求症状持续至少6个月,但为了不延误治疗,目前多数学会采用更短的持续时间标准(如>6周)作为临床诊断门槛。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(CUA)近年来也高度关注IC/BPS。尽管我国过去缺乏专门的IC指南,但2022年由中西医结合学会牵头制定了中国IC专家共识,对IC/BPS的定义和诊疗进行了规范。该共识强调:IC是一种慢性、非感染性的膀胱炎症性疾病,以慢性盆腔疼痛以及尿急、尿频为主要临床特点,同时尿常规和尿培养反复阴性。可以说,这一定义与国际接轨,突出了排除感染和症状复合体两个关键点。共识中同样建议了详细的诊断步骤,包括必要时采用膀胱镜检查来协助诊断和分型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IC专家共识结合了国内中西医结合的特色,提出多学科诊疗模式的重要性,也为后续治疗提供了指导。总体而言,无论AUA、EAU抑或中国专家共识,各大权威指南在IC/BPS的诊断原则上高度一致:即“临床判定+排除其他+客观检查支持”。遵循这些标准,既可提高诊断的准确性,也为治疗打下了正确的基础。
治疗概览
多维度抗击膀胱之痛
尽管间质性膀胱炎的治疗目前尚无“根治一招”,但多年来的研究和临床经验已探索出一套综合的缓解方案,帮助患者逐步夺回生活的掌控权。正如黑夜中总有星光相伴,对于IC/BPS患者而言,各种治疗手段如同繁星,组合起来可以照亮希望的天空。治疗需要个体化、多模式并举,通常需要多学科团队合作,这已成为共识。我们按照从保守到侵入的顺序,来概览目前主流的治疗策略:
1. 行为和生活方式疗法:这是IC/BPS治疗的基石和起点。很多患者通过调整生活习惯可以显著减轻症状。首先是饮食管理:医生会建议患者避免摄入可能诱发症状的食物和饮料,例如咖啡因饮品(咖啡、茶、碳酸饮料)、酒精、辛辣刺激的调味品、酸性水果汁等,因为许多患者报告这些**“膀胱雷区”会加重疼痛和尿急。不少患者戏称这是一场“饮食上的忌口修行”,但确有助于减少症状发作频率。此外,膀胱训练是行为疗法的重要一环。由于IC患者往往习惯一有尿意就立即如厕,膀胱长期处于低容量状态反而进一步缩小了容量。通过循序渐进延长排尿间隔**(如本来30分钟尿一次,逐渐延长到45分钟、1小时),可以锻炼膀胱的容量耐受,提高储尿能力。这种方法需在医师指导下进行,避免过度憋尿引起不适。应激管理和心理支持也不可或缺:慢性疼痛和不良情绪互相影响,患者可学习放松技巧、减压方法,必要时寻求心理咨询,改善应对疼痛的能力。最后,盆底肌肉物理治疗对很多患者有益。经验丰富的物理治疗师可以通过手法按摩、牵伸等方式松解盆底、下腹部和髋部过度紧张的肌肉筋膜,释放触发点,降低肌肉反射性的紧绷,从而缓解部分患者的盆腔痛和尿急症状。需要强调的是,应避免让IC患者做一般的盆底肌锻炼(比如凯格尔运动),因为他们的盆底往往已经过度紧张,再强化只会适得其反。整体来说,行为疗法如同夯实地基,不仅副作用最低,而且为后续药物和手术疗法奠定更好的效果基础。
2. 药物治疗:药物是IC/BPS综合治疗中不可少的重要工具,包括口服药物和膀胱内药物灌注两大类。根据AUA和EAU指南,目前常用的口服药物主要有以下几种(按字母顺序):阿米替林、西咪替丁、羟嗪、戊聚糖多硫酸酯(PPS)。这些药物各自通过不同机制帮助缓解症状:阿米替林是三环类抗抑郁药,具有镇痛和镇静作用,可改善膀胱过敏状态;西咪替丁是一种抗组胺H2受体拮抗剂,可能通过抗炎途径缓解症状;羟嗪是镇静抗组胺药,尤其适用于有过敏体质或夜间瘙痒难眠的患者;戊聚糖多硫酸酯则被认为可以修复膀胱黏膜的GAG保护层,减少尿液对膀胱壁的刺激。以上四种药物在2014年AUA指南中被列为推荐的口服疗法(无优先级之分),也成为2018版EAU指南的一线用药选择。需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,其中阿米替林因其副作用(如口干嗜睡)需要从小剂量逐渐增加;PPS口服安全性总体较好,但近年来有报告提示其长期使用可能与视网膜黄斑变化相关,因此AUA 2022指南特别提醒医师和患者知晓这一风险。除了上述药物,一些患者症状突出时也可酌情使用镇痛药(如解热镇痛剂、NSAIDs,甚至短期阿片类)来缓解疼痛,原则上按照慢性疼痛管理规范使用。
对于IC/BPS这个“膀胱局部病”为主的疾病,膀胱内灌注给药是一项颇具特色且有效的治疗手段。灌注治疗通过导管直接将药物送入膀胱,并保留一定时间,以高浓度作用于膀胱黏膜,既提高疗效又避免全身副作用。常用的灌注方案包括:二甲基亚砜(DMSO)、肝素、利多卡因等单独或联合灌注。DMSO是唯一被美国FDA正式批准用于IC的膀胱内用药,具有抗炎、止痛和增加细胞渗透性的作用,不过其特殊的大蒜味让不少患者“闻味色变”。肝素用于补充GAG层,常与利多卡因(局麻药,可局部镇痛)配合灌注,以在修复黏膜的同时立即缓解疼痛。不少中心采用“鸡尾酒疗法”,将肝素+利多卡因+碳酸氢钠混合灌注,每周一次,疗程数月,看是否改善症状。研究表明相当比例患者从膀胱灌注中受益,症状减轻、排尿间隔延长。在国内中西医结合共识中,亦推荐了包括透明质酸钠灌注、皮考硫酸灌注等新型方案,旨在恢复膀胱黏膜屏障和抗炎止痛。
3. 手术及介入治疗:当保守治疗难以奏效时,可考虑一些有创的干预措施来扩大膀胱容量、减轻病变。一项历史悠久且仍被应用的治疗是膀胱(水)扩张术。在麻醉下,用生理盐水将膀胱缓慢充盈并维持一定高容量一段时间,然后放空。这种机械牵拉可以一过性地拉伸纤维化的膀胱壁、暂时提高容量,许多患者在术后数周内症状明显减轻。其机制可能与牵拉神经末梢、打断疼痛信号传导有关。AUA指南将低压短时的膀胱扩张作为一种可选治疗。不过,扩张效果往往不能持久,数月后症状可能反弹,需要重复操作。而且过度高压或长时间扩张有导致膀胱破裂或出血的风险,因此需要有经验的医师掌握度。对于存在Hunner溃疡的患者,有一种针对性的手术称为病灶电凝/激光烧灼术。通过膀胱镜,用电灼或激光将这些溃疡病灶烧灼消融,或者局部注射激素(如曲安奈德)促进愈合。临床证据显示,处理Hunner病变能够显著缓解此类患者的疼痛和尿频,效果往往比一般治疗更明显,因为Hunner型IC本就是一个特殊亚型,病变局限明确,处理后膀胱炎症负荷大减。AUA指南将电凝Hunner病灶列为强烈推荐。另一种新兴的微创治疗是肉毒毒素A膀胱壁注射。通过膀胱镜,在膀胱壁多点注射少量肉毒毒素,可以抑制局部神经末梢释放神经递质,降低疼痛感,并放松膀胱肌肉以增加容量。小型临床试验显示其可改善部分难治性IC患者的症状。但注射后可能造成一过性尿潴留,需要患者能够接受间歇导尿的可能性。因此将肉毒毒素作为可选择的三线治疗。
4. 神经调节与重建手术:对于那些经多种疗法仍无法取得满意效果、生活质量严重受损的顽固病例,进一步可以考虑神经调控和外科手术。骶神经电刺激(SNS)是目前应用较多的神经调节技术,相当于给膀胱神经装上“起搏器”。手术在患者骶骨区域埋置一根电极靠近支配膀胱的神经根,连接一个埋藏的脉冲发生器,间歇性发送电刺激以调节神经反射弧的兴奋性。SNS已广泛用于治疗顽固性OAB和尿潴留,近年来也扩展用于IC/BPS,被认为可以减轻疼痛和改善排尿症状。一些IC患者接受SNS后报告尿急缓解,镇痛药使用减少。但SNS对IC的疗效因人而异,费用高昂且需定期更换电池,患者需谨慎权衡。除了SNS,针灸等中医神经调节方法在国内也有探索应用,纳入多学科治疗体系中。外科手术作为最后的防线,仅在极端情况下考虑,包括膀胱扩大或替代术以及膀胱切除尿流改道术。膀胱扩大术是用一段肠道组织嫁接到膀胱上,以增加容量、降低膀胱内压力;而膀胱全切除则是切除病痛来源的膀胱,改由回肠代膀胱或尿管皮肤造口引流尿液。这些大型手术创伤大、并发症多且疗效并非绝对可靠,因此无论AUA还是EAU指南都将其视为万不得已时的最后手段。AUA在2022年更新中特别指出,重建手术对于IC/BPS的收益风险比尚不明确,应仅在其他一切疗法均失败且患者痛不欲生时考虑。可以说,对绝大多数患者而言,我们期望不必走到这一步。
需要强调的是,IC/BPS的治疗没有“一招鲜”,往往需要多种手段联合,并根据患者反馈不断调整。患者的参与和共情对于治疗成功至关重要。医生会与患者充分沟通,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,让患者理解各种疗法的作用机制和现实预期。有时需尝试反复、多轮治疗,比如口服药物的组合调整,灌注治疗与行为疗法并进等。一项共识指出,大部分IC患者经过规范治疗后可以达到症状缓解或部分缓解,虽然可能反复发作,但每次发作我们都有新的方法去应对。因此,患者不应失去信心,而应该将IC视为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,与医护人员携手,找到最适合自己的“配方”。
在治疗的道路上,科普和支持同样重要。患者需要被告知:他们的病痛是真实的,并非无中生有;现代医学已经承认了IC/BPS的存在,有一群专家在持续研究这一领域。许多国家和地区成立了IC/BPS患者协会和支持组织,提供交流平台和心理支持。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公益科普(例如本文正是面向公众的科普一环),旨在提高大众对IC/BPS的认识,帮助更多“沉默的疼痛者”发出声音。正如一位IC患者所言:“知道自己并不孤单,比任何药物都更令人宽慰。”
间质性膀胱炎,这个名字听起来陌生又拗口,但其折射的其实是人类在对抗慢性疼痛道路上的共同课题。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,用诗意的关怀去倾听患者的心声。从了解定义到掌握鉴别,从遵循指南到灵活治疗,每一步努力都在缩短误诊的阴影,让更多患者早日走出黑暗。或许,彻底治愈IC/BPS的答案尚在未来,但每一个今天,我们都在朝那个方向迈进。而对于那些正被膀胱之痛纠缠的人们,希望通过这篇科普,能为您带来一些启发和信心:你并不孤单,这隐秘的疼痛正在被看见;科学与关爱终将携手,为你守护光明的未来。
参考文献:
Clemens JQ, 等. J Urol. 2022;208(1):34-42. (AUA指南对IC/BPS的流行病学定义)
王亮. 知乎专栏. 间质性膀胱炎(2020). (国内专家对IC误诊率的讨论)
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委会, 等.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. 2022;28(6):757-762. (中西医结合诊疗IC专家共识)
蔡国钢, 等. 临床与病理杂志. 2019;39(6):1304-1310. (IC/BPS发病机制综述)
娄文佳, 朱兰. 中华医学会科普部. (2025). (IC/BPS科普文章,症状与治疗)
Mayo Clinic妙佑医疗. 间质性膀胱炎:症状与病因. (2021). (权威医学机构对IC症状的描述)
Clemens JQ, 等. AUA IC指南(中文版). (2022修订). (AUA指南关于IC鉴别诊断和评估)
AUA指南小组. 间质性膀胱炎诊断与治疗. (2022). (AUA指南关于排除检查和尿动力学)
Clemens JQ, 等. J Urol. 2022;208(1):34-42. (AUA指南要点,中译版)
中华外科杂志编委. 2022 AUA IC指南更新解读. 中华外科杂志. 2024;62(2). (对最新AUA指南的解读)
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ciety (ICS). IC/BPS定义. (2018). (ICS关于BPS的定义标准)
Clemens JQ, 等. J Urol. 2022;208(1):34-42. (AUA指南对IC/BPS的流行病学定义)
王亮. 知乎专栏. 间质性膀胱炎(2020). (国内专家对IC误诊率的讨论)
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委会, 等.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. 2022;28(6):757-762. (中西医结合诊疗IC专家共识)
蔡国钢, 等. 临床与病理杂志. 2019;39(6):1304-1310. (IC/BPS发病机制综述)
娄文佳, 朱兰. 中华医学会科普部. (2025). (IC/BPS科普文章,症状与治疗)
Mayo Clinic妙佑医疗. 间质性膀胱炎:症状与病因. (2021). (权威医学机构对IC症状的描述)
Clemens JQ, 等. AUA IC指南(中文版). (2022修订). (AUA指南关于IC鉴别诊断和评估)
AUA指南小组. 间质性膀胱炎诊断与治疗. (2022). (AUA指南关于排除检查和尿动力学)
Clemens JQ, 等. J Urol. 2022;208(1):34-42. (AUA指南要点,中译版)
中华外科杂志编委. 2022 AUA IC指南更新解读. 中华外科杂志. 2024;62(2). (对最新AUA指南的解读)
International Continence Society (ICS). IC/BPS定义. (2018). (ICS关于BPS的定义标准)
欢迎
发布于:浙江省兴盛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